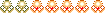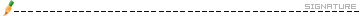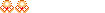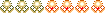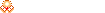幸运的,在外面十天,除了在尼洋河边睡觉时下雨,其他都是好天气,雨衣和包罩都没有派上用场。
拉萨是“日光之城”,曾导说北京的大晴天,紫外线强度是30%;而日喀则地区的阴天,紫外线强度也有70%。
可是,我喜欢大大的太阳。
周末,一个懒觉醒来,往往十点之后了。拉开窗帘,如果这时有很好的阳光照进屋子,我铁定张口就唱:“太阳光晶亮亮,雄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一边在磨蹭,一边反复唱:“不爱劳动不学习,我们大家不学它……”
我跟Nicole一说这事,她说她也是!每次上班前,她都唱一休:“钟声铛铛响,乌鸦嘎嘎叫,和尚的修行时间又来到……”
接下来的几天,我也跟着她唱一休,渐渐把她标准的唱腔硬扳到和我的走音一样。
去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那天,艳阳高照。
太阳把我的脸烤成一块肉饼,仿佛还呼呼冒着热气。
于是,外出时,我总是给肉饼戴上太阳镜,围好头巾,再顶上宽沿的遮阳帽。
布达拉宫(Potala Palace),在拉萨的市中心。
我们都觉得它没有想象中得宏伟,它的脚下,穿梭着车辆,充斥着商店。毛毛说在她印象里布达拉宫应该更高大,更雄伟。
我也是。
更让我明白,现实和想象总是存在着差距。
可是,小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几年后我会来到它的面前。这样的感觉似乎很奇妙:以前在杂志画册或是历史地理课本上看到的地方,现在可以一个一个亲自到达。
就像羊皮筏子,小学在语文课本上读过,去年夏天就在兰州见着了。
布达拉宫限制游客人数并规定参观时间,即使在五一、十一这样的黄金周,每天最多发放2000张购票凭证。
在广场等候进去的时候,大家百无聊赖地拿着相机到处捕捉镜头。
红宫和白宫,像是大的古堡,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很多转经轮磕长头的人,都是朝着正当中的红宫方向下跪的。
有一位老妈妈,领着一个小女孩,坐在树荫下休息,并不说话。Nicole给了她两颗糖,过了一会儿她向我招招手,这样的示好让我受宠若惊,蹲在她面前,她把小手主动伸给我握着,更让我有点轻飘飘了。
同伴开始谋杀快门。
回来以后在网上看到建国拍的一张很是让我心动:老妈妈和小女孩温顺而专注地看着我,眼神非常单纯、清澈。
五一在西藏,就布达拉宫人比较多,其他的地儿人都出奇得少,很称我意。
跟着人群在里面兜来兜去,周围有两三个向导同时在介绍,一样的东西说得又不大一样,感觉有点头昏。藏传佛教很是复杂玄秘,王导说如果不研究十年以上,是不可能把藏传佛教说到精透的。
布达拉宫的厕所太有特色了,门口藏文是看*的,还好旁边有烟斗和高跟鞋区分男女。掀开布帘,穿过狭窄的过道,像小教室一样大地方全是蹲坑,蹲坑下面就是高高的山仞。在原来松赞干布居住的这样神圣的地方一泻千里,实在是太壮观。
厕所出来,看见一个外国lady暴晒于阳光下,坐在台阶上看一本书,是Lonely Planet系列的Tibet。呵呵,这算不算按图索骥呢。
宫殿寺院都建在山上,大概是让人们对它“高山仰止”,可前前后后的游人中不乏穿细高跟鞋的强人。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到有一个小姐对旁边人说“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好玩,累死我了,蛮好不要来的”。妈的,是谁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你,又捐给民航钱,让你万不得以、极不情愿才来到这里的啊!
宾馆隔壁有一家超市,名字很革命,叫“红旗连锁”。我和Nicole基本上每天下午都去那买酸奶,和蒙牛的促销员打得火热,她又是送抽巾纸又是送陶瓷杯,弄得怪不好意思的。
在自动扶梯上看见一对老外夫妇,是外国老夫妇了,都是标准的大肚子大屁股那一类。老先生勾着老太太的胖腰,亲热地在老太太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每次在各个景区,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都是老外。应该都是退休了以后一起来到中国旅游的吧,满头银发了,还那么恩爱,很让我羡慕和感动。
在我看到的西藏旅游指南的注意事项上,基本都写着有高血压*病糖尿病的游客,不宜进藏。我不知道国外的书刊介绍有没有这一条,有没有让游客慎重慎重再慎重的警示,而来到西藏的大腹便便的老外夫妇有没有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的。
我喜欢八廓街附近的小巷,都是藏式民居,窗台上放着一盆盆花,开得欢快。
有偶尔走过的阿卡,有嬉闹的孩子,有睡着了的卖肉师傅,还有一个小寺。
周围的房子基本上都是白色灰色的,当一座明*的小寺突然站在我们视线里,我和Nicole还是有些吃惊的。走上陡陡的楼梯,里面只有一个阿卡,正在认真地往灯盘里添酥油。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小和尚……”说的应该就是这个。
Lilian,Sunny,Conrad和Berrick他们去了色拉寺,那会儿我和Nicole正在宾馆的阳光里写日记。现在忽然看到了并无期许的小寺,觉得心里也很满足。
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庙,是拉萨的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甘肃的拉卜楞寺,青海的塔尔寺。
我只去过两个,哲蚌寺和塔尔寺。塔尔寺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诞生之地,而哲蚌寺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寺院,曾住有一万僧人。
哲蚌的藏语就是“米聚”,房屋都是白色的,仿佛是白色的米堆,象征着繁荣。
除了如梭的藏民,游人非常少。
他们手里拎着保温瓶热水瓶或者拿着酥油的口袋,看到佛像面前的长明灯,就虔诚地添上一勺酥油或是倒上一点酥油茶,口中念念有词,小心翼翼。供桌上大多是角票,你可以放五元纸币进去,再找出四元九角的纸币拿走。
佛祖宽容地看着信徒,目光温和慈祥。
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比起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最能打动我的心。如果那天的阳光再热烈一些,那就太完美了。
“玛吉阿米”是大昭寺旁边一家著名的藏餐厅。它的著名,是因为六世达赖仓央嘉错曾经在这里遇到了一位月光女神般的美丽姑娘。
去年年底看电影《情癫大圣》,里面有一句台词“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配当时唐三藏的背影。回家以后查了查诗句的出处,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仓央嘉措的名字。再查了查他生平,原来是一个和小峰峰演的三藏一样,又爱佛祖又爱女人的传奇男子。
在玛吉阿米买了本仓央嘉措的情歌,后来发现“最好不相见,免我常相恋,最好不相知,免我常相思”这样极富现代气息的诗,竟也是出自他手。
据说,仓央嘉措任达赖喇嘛之后,在布达拉宫旁开了一个边门,晚上就溜出来到玛吉阿米和心爱的女子幽会,于破晓前悄悄回到布达拉宫,直到有一天下雪,侍从看到留在雪地的足迹,进而发现了这个秘密。
藏族人认为这不过是个传说,可我相信这确有其事。
盛名之下的玛吉阿米,我和Nicole都不喜欢:人多、嘈杂、有烟味、天台不漂亮。
多多姐、王导和司机王师傅,都喜欢这里,在拉萨的每天都在里面泡着,痛快地享受着酒。
感受是很私人的东西, 每个人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都是发自内心的,无关乎这个地方的好坏。
我和Nicole有两天的下午都泡在Gallery & Bar的天台,离玛吉阿米不远。
那儿有干净的天台,漂亮的油画,有啤酒青稞酒和酸奶,我们努力把自己的肚子塞成杂货铺,然后,发呆,写明信片。
Lawrence说他有个师妹,曾经在西藏旅行时帮助过一个老外,借给他两三百块钱。回到北京后都把这事淡忘了的她,有一天收到国外寄来的一幅画,上网一查那幅画的作者竟然是享誉艺术界的一位现代派画家,响当当地在纽约开着画廊。
Gallery的老板坐在我们隔壁桌,扎一小辫,满脸沧桑,抽着烟喝着酒,说着艰苦创业史 。我脑中根深蒂固的艺术家形象就是他这样的。
也是有传奇的一幕的:一个高个年轻老外和一个藏族大龄女子,一边喝酒一边说着藏语。然后,两人抱在一起很久。接着,藏族大姐姐走了,老外在身后响亮地叫她的名字,她头也没回。老外留下一个人,边喝酒,边和藏族服务员说话,边大声哭泣。
我不得不展开我丰富的联想:这个老外为了她翻山越岭,为了她学习藏语,为了她留在了西藏,一转身,她却不在这儿了。
大昭寺(Jokhang Temple),我去了两次。
所有藏族人磕长头最后的终点就是这里,因为供着最著名的一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由文成公主从内地带到西藏。
很多磕长头人,在大殿前五体投地,并忍不住热泪横流。
在这个头顶三尺有神灵的地方,时间像是回到了中世纪。突然觉得,人在自然、历史、信仰面前显得特别渺小。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是有区别的,光从磕头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们用磕头虔诚地碰一碰供桌或是佛龛。
药王山上边有一块石头,据说蹭一蹭就可以包治百病。所以,很多很多人,头痛蹭头、脚痛蹭脚。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喇嘛,后面跟着一帮人走过来。看见我在一边愣着,忽然拉着我的手来到一扇门前去触摸门上的一块地方,然后又拉我到一根柱子前示意我用额头去碰。莫名其妙地做了这些事,后来看到很多藏族人也如此,顿时觉得自己镀了层光。
这次弄清楚了班禅活佛和达赖喇嘛的区别,还有并不是所有寺院里的红衣僧人都有资格被唤作是喇嘛的。王导说喇嘛相当于博士级别,其他的僧只能被称作是“阿卡”,嘿嘿,于是我们理所当然叫大猫为大猫喇嘛。
有个小“阿卡”,抱着大昭寺的一根柱子在唱“吉祥三宝”,可爱极了。
拉萨有大昭寺和小昭寺。其实,最先大昭寺供奉的是尼泊尔的尺尊公主,松赞干布的第一任妻子,小昭寺供奉的才是文成公主。
导游说文成公主并非皇帝的亲生女儿,我嚷嚷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如同王昭君,皇帝的骨肉往往都留在身边赏赏小花,听听小曲,哪里会送到蛮夷之地去和亲。
不知道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否会想起故乡的月亮,也不知道她究竟是爱上了那个男人还是爱上了那片土地,抑或是先爱上了那个男人,再爱上了那片土地。
文成公主至少是决绝的,她抛在青海的两面铜镜变成了日月山,隔开了大唐中土和青藏高原,将自己的美丽和哀愁都永远地留在了西藏。
松赞干布是藏族人心目中的英雄,英雄总是值得优秀的女人来爱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7 13:17:47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