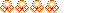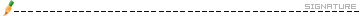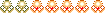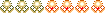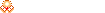D1 2005.9.30 晴
工作上突发的紧急任务使我调休不成,我按捺住兴奋的心情使劲将我的脚紧贴着地面,直至团中央的领导视察完毕。
打包的过程一直让我感到迷惘,很长的时间都在带与不带之间斗争和徘徊。初步打包之后,包的重量是30斤,超过体重的1/4,直逼1/3。无奈之下开始减负,放弃腐败物资若干,将KIKKON COOLPIX 5000换成SONY M1,力求轻便。放弃2斤重的厚型冲锋衣,用班尼路的雨衣代替(后被证明此举有欠高明)。再次过秤之后,包依旧有30斤重,十分错愕。食物连同水的重量居然有14斤。念在第一天轻装上徽杭,头天可将水与食物解决一半,遂未将其削减。
晚上九时许,我背着我60L的LUNA 60穿越大半个城市,赶到八万体1号扶手发车地,一路上接受无数异样的眼光,有些隐隐透着为孱弱女子背包的冲动。不晓得是我太瘦了,还是包看上去太沉了。
一眼望去,近百个盼着发车的驴子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看到地上大大小小的旅行袋甚至是塑料袋,暗暗想着:这对他们来说也许会是一场艰难的旅途。等camel的间隙,和两位去龙王山的MM唠嗑,从它们的眼神里,感受到第一次出行的激越,仿佛这趟旅途也变得越发神圣起来。
确认了领队之后,大部队开始登车,接受了3月出行时的教训,懂得了在车上要尽量积攒体力,枕上气枕一个,寻找最舒适的睡姿,捕捉偶然冒出的梦呓,睁眼便看到大巴的车灯射穿无尽的黑暗,身后是沉沉睡去的老驴和兴奋健谈的新驴。在时针逼近午夜零点的那一刻,我晃晃悠悠地睡去。
D2 2005.10.1 晴
大巴稳妥地停在绩溪车站的对面,灰蓝的天色让人辨认不出时间,打听得到消息,五时许。对面的早餐铺子尚未营业,空气中有一丝清冽的气味。随处走了走,报厅里只有绩溪县的地图,清凉峰的地形图则简略得连我都能画。车站里厕所的昏暗程度一如既往,长凳上躺着等着早班车的困倦旅客。
萝卜丝饼和热粥,我的胃感到异常的温暖与充实。一边的Maczhou没扒几口食物,不足以补给一天的消耗,我提了个醒儿之后径直跑去对面宾馆大厅的沙发上蹭睡。间或跑进跑出好些人,大抵是混进宾馆洗漱的。宾馆外驴子们的交谈像是变奏曲。
六时许,大巴抵达伏岭镇。我打量了半天,终于认出三月份卖给我劣质雨衣的小卖部,似乎已经变了样子。好在找到下行的道儿,走在队伍前面。轻装的感觉煞是奇怪,一身还算比较专业的装备配上一个美特斯邦威的包,多么有特色的组合,也算是“不走寻常路”了。打身边经过的领队小爱问我Luna 60上哪里去了?车上躺着呢呗。他说他的很多装备与我雷同,细细打量,果真如是,他笑了笑走到了队伍的前头去了。我的相机似乎是最耐不住寂寞的,在快干裤的口袋里激动地跳跃着,好象真的要冲破出来。稻垛、秋收和金黄,时节果然是不同了。倘若再来一次,是否还一样有新意?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可以做到不走走过的路。在我看来,一个地方,如若来第二次,便有一种不同一般的感情了。起码这次走徽杭,没有了上回的茫然和无望,永远也不知道哪里是终点。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成了某种提示,即使我经常记忆错位。
前段路走得有些辛苦,石阶路和烈日是我的死穴,行进途中居然出现了长达两分钟左右的眩晕,在补充了糖粉和水之后迅速得以恢复。庆幸自己这次没跑长线,否则必定成为包袱。
在任何休息点停留后,势必要早别人一些出发,以保持心理上的优势。Camel永远在我前一些的地方走着,步伐不快,却像永远也赶不上似的,想到“夸父追日”这个成语,然后觉得好笑。不晓得当年雪岩兄从安徽挑盐去杭州卖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伴儿。倘若只身一人,岂不孤单?
当大军在溪水中尽情嬉水之际,我和Camel已经将午饭迅速解决。肉、面包、橙子和苹果,即便在城市里,我也没有如此考究的午餐。包又轻了大半,安静地趴在我的肩头。
十一时半,再次起程。
“之”字行路终于来临,短暂的一截儿,没有什么感觉。这一段登山杖很好使,我再一次感受到高科技的威力。
十八龙潭休息良久,买下一瓶矿泉水和两条黄瓜。松开鞋带,眯着眼睛看高处树叶间穿透过来的阳光。手使SONY707的MM很健谈,跟我讲它与717之间的区别。相机机身上那一块旧了的邦迪是相机的的伤口和荣耀。长头发的女孩用一本大开面的本子记录着行程,完全不受周边的打扰。向导骑着摩托飞身而去,落下了一阵阵的惊叹……
再次起程,体力恢复大半,大肆自恋自己是耐力型选手。
蓝天凹还是变了样子,俨然景区模样。只是徽杭之家的竹屋还在。记得上回来的时候,夜里,我和小饼不愿跑去黑咕隆咚的茅厕,就跑来屋后“灌溉”,由于搭建小屋的竹子不很密集,我们还心惊胆战。其实屋里的腐头们正忙着烤火,什么都不会在意。
从远处唤了几声小黑,未见踪影,心里面有隐隐的思念。那个时候,它是我们浩浩40大军的宠儿。
始终还是没走进徽杭之家,照了相,纪念这个住过一夜的地方。仰望苍穹,此时的天空蓝得很纯净。
蓝天坳客栈,大伙儿忙着补水,领队呼吁大家往上走走,于是我站在抛物线的顶端看到云朵像是开在山头的花。山风在我身边猎猎作响。在没有方向的风中开始跳舞吧,或者紧紧鞋带听远方歌唱……
下山的路很好走,在半途遇到徽杭之家的女主人,Camel竟一眼就认出了这位老妇人。她告诉我们小黑在今年的五月弄丢了,也许是跟一些驴子走了,刚丢的时候,她哭了整整两天两夜。老人家的眼睛里再次涌出了怆然,于是我们立即转换了话题。听老人家说,当晚会有100多人在徽杭之家扎营,十一期间300多驴子都要在那里歇脚。老人脸上的汗滴在皮肤的沟壑间流淌。话别之后,我依旧在怀念那条叫做小黑的狗,在宿营的第二天,它送我们一路下山,在绵绵的细雨中伫立在永来村的村口目送我们走远,多么通人性的狗呵!Camel想起了她那独自在家的“包子”,巴望着早些回去看它左右晃动的尾巴。我在想:有时候,相处得很久的人未必有那么深的感情,可以在刹那抽去,不留任何眷恋和怀念,也不会徒然想起,但对一直陪伴着的宠物或者物件,却会有那么强的依赖,倘若丢失,就不再习惯。人类就是那么奇怪的动物。
在半途的竹亭碰上一群正在重装反穿的驴友,随意闲扯几句,给亭子和迎客松留影,也算是过往的纪念。狐狸带队的时候,带我们在这里休憩了好一会儿,让已经继续下撤的同伴狠狠抱怨了一阵。
路遇一山民,得知我们第二天要登清凉峰时,警示我们要注意大风。老汉在山里生活了几十年,每日的工作是维护山路,这山是他的根呐!
终于踏上了永来村——古道另一端的小村落,我还依稀记得村里的每一条小道。夕阳西下的时候,这宁静祥和的村里满是收获的气息。Camel正忙着研究各家门上的对联,我则在找寻着上回买可乐的小卖部,回忆这东西有时候真的是一种小小的牵绊。十块钱一包的山核桃依旧在贩卖,又有大拨的人正在掏钱。
走出村子,龙潭大酒店附近的营地就到了,众人立即作鸟兽散。底气十足地说着“将自虐进行到底”的驴儿们迅速向饭堂和旅店狂奔。我和Camel则挑中了一户人家的水泥平台扎营。
夜色如幕布一般很快便铺开了,我甚至还看到了天边的启明星。打开头灯与领队擦身而过的刹那,只是看到深色的轮廓而已。刚买到的芭蕾舞鞋承载我整个身体的重量,欢快地奔跑着。
悻悻地洗了个郁闷的冷水澡后,赶上饭店里最后一些粮食做晚饭,有鱼有蛋,心满意足。遇上来自同济的那些驴子,铁定我们第二天不能重装登顶,不能确定是不是去年在龙王山遇到的那群。
静谧的夜在忽高忽低的鼾声中凭添了几许人的气息。身上由于防晒霜与汗液混合而至的过敏瘙痒已消失怠尽。管Dennis借来的防潮垫像一张舒适的床,不一会儿,我便进入了酣眠……
午夜的时候被响动惊醒,仿佛是有人在有频率地牵扯着外帐,怀疑那并不是风,由于睡前屋主人家的小姑娘说的一句“晚上你们当心,这里时常有人溜进来”这一句,给我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心理暗示。我和Camel的包和鞋子统统在帐外,让人有些担心,不过警觉仅仅维持了十分钟,在疲累的侵袭下,我再次重重地跌落梦境中。
D3 2005.10.2 雨
六点醒来,同在平台扎营的驴儿们都已经在收拾东西了,劈头盖脸被肿着眼睛的Camel骂“猪头”。我们的鞋和包好好地在帐外躺着,不曾有被挪动的迹象。
早晨的时候,天气晴好。为了重装登顶,我和Camel均以毅然决然的姿势放弃着可带可不带的物件,仿佛要奔赴前方的沙场,为了顺利地归来,需要做某些割舍。我掂了掂被丢出大包的东西,大概有三斤重,其中包括了两块方腿和一根熏肠。Camel就着2L的水袋猛喝水,以期让背上的重量全上肚子里去。
在清早的阳光里,有人动情歌唱,多少沾染了山里的民风。我在想,什么时候自己能沉稳地像眼前的那些山,无论刮风下雨,都巍然不动。
山里的天,像孩儿的脸,当大巴沿着盘山公路把我们送至清凉峰山脚下的时候,天已经阴了大半,想起昨日老汉的话“午后有雨,出行小心”。随即又闻噩耗“山里大风,轻装登山”。再一次捣鼓我的行囊,二十五块钱的美特斯邦威的小包再次派上了大用场,回到上海它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可以功成身退了,比Osprey的折旧划算多了。再次问Camel带些什么,她说不带大包,我的行装随我,她管不了。也是,户外教会人很多东西,其中包括:自己做决断,并为你的决定负责。
十一时许,山下用餐,看到Camel已经开始往山上走,没有跟上。
攀登的过程有些许辛苦,希望把有氧呼吸的时间尽量拉长,保持着两步一呼两步一吸的节奏。在半个多小时后,依旧是口鼻并用了。汗水沿着脸颊滑落到下巴尖儿上,然后滴落在快干裤上。山里起了浓雾,抬头都看不到山顶。也好,望山跑死马!我心安理得的只顾脚下,相机在防水袋里昏睡,不忍让它出来和水气抗争。
跟着爽朗的“压寨夫人”与和顺的“占山为王”走了很长一段,由于三人的行进速度比较一致,也挺谈得来,一路上并不觉得累。路遇好几路反穿的驴子,告诉我们前方还有2/3的路程,边上经过的新驴mm快乐的告诉我们快到顶了,领队说还有不多路了,没好意思说穿。领队们都懂得在适当的时候给你来一剂强心针。瞧,这两位mm走得多带劲啊!
大约在下午近两点的时候,大部队抵达景区路线尽头的小木屋,山雾弥漫,霪雨纷纷。这时已有几名驴子下撤山脚,前面已经是泥泞的野路。昏暗的天色和迫近的台风让领队们又另下决断,大部队下撤,有头灯或者手电想继续往上的可以再走,三点半无论有没有登顶,统一下撤,不得有异议。我毅然拿出头灯站在愿意继续攀登的队伍里。这时,队伍中一共有八人,女生两名。Camel站在高处叮嘱我小心,我将多余的东西装在防水袋里交给了她,身边剩下水、一小部分食物、雨衣、头灯和求生哨。
再一次踏上征程的时候,领队小爱拍了拍每个人的肩膀,似乎是一种无声的鼓励。大部队在我们身后响起无数掌声与喝彩,仿佛是在送走出征的壮士。
石阶路完全走完的时候,回身一望,身后还有长长一排的驴子,报数之后才发觉总共上来了30人,心里有暗暗的小庆幸。
原先计划中的扎营地到了,那是一片还算开阔的草地,在这样的暮气下,更像是一块沼泽。领队又一次征求意见,大多驴子支持继续上。
队伍保持着密集的队型迂回前进,在我前后方是两件亮蓝和正红色的冲锋衣,很是鲜明。没带冲锋衣被证明是一个极大的失误,班尼路的雨衣里弥漫着水气,它像一个巨大的蒸笼包裹着我,决定挣脱它的禁锢。Montrail鞋在一片泥泞中有些打滑,鞋底的坚硬程度和抓地力不可两全。
风雨中的一路欢歌让这片山头开始闹腾起来。
半小时后抵达接近山头的斜坡,山风开始增大,细雨随着风向向着南方飘摇。领队小眼睛建议大家下撤,话语中多了几许命令的语气,其实也是应该。我忽然想起在凄风苦雨中的怒海狂风和他头顶上的那片阴云。猜想着他遇难前的无助。安歇吧,天堂里没有悬崖。
大伙儿在风雨里照了张特荣耀的合影之后便开始下撤。
小木屋里,小爱、高义两位领队和一些没有上行的驴子还在守侯,感动不已。我拨开湿透的头发,和牛奶男DD两人将最后几根拇指肠消灭了。
下山的路不太好走,地滑是捷径的代价。由于打滑,我空穴来风地吼了两声,最终摇摆着楞是没倒下。走在前面的MM一步一个颤。我的前脚掌很痛,登山杖扎得很深。队伍挨得很紧,不时有人发出几声有惊无险的惨叫,这个时候,别跟我谈什么“多米诺骨牌”。
在“亲爱的平路,我们来了”的欢呼中,我们顺利踏上盘山公路,我浑身上下只有鞋子里是干的,脚已经达到自动化程度,仿佛是刚脱去了溜冰鞋的孩子,一走路便好像踏在云端。
camel在大巴旁迎接我,搂着我说“辛苦了”,其实并没有感觉多累,只是一停下来,浑身冰得很。
车上,我穿着我湿淋淋的衣裤,披着Camel的冲锋衣抵挡着车里从各个出风口奔涌而出的冷气。车子下山时,前方能见度不过10多米,连续弯路多得出奇。我蜷缩着身子看着窗外的景色,已经分辨不出那是来时的路。车里开始播放朴树的《旅途》,我跟着轻声地合:“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路过幸福,路过痛苦。路过另一个人的温暖和眼泪,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旋律像一只温暖的手触碰到*最柔软的部分。
大明山脚下的旅馆地下室与大厅内的扎营宣布着新一次腐败的开始。晚饭时的困倦与偏高的体温在一场热水澡中烟消云散。一杯热姜茶在握,与Camel走了一段下行的路,听潺潺的溪流淌过,这样的感觉已经很久不曾有过。倘若还在城市,这个时候我应该还在逼迫自己静下心来,却还是浮躁地加着班;或是在喧闹的网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无谓的人说着无谓的话。刚刚邀请我上馆子的那两个驴子现在一定吃得很香吧。在无边的夜色中,旅店外面踱步的大狗乖巧温顺地低着头……
在与落草为寇、Noliper和占山为王灌下几口红星二锅头之后,借着酒兴,提出玩“杀人”。召集了一帮人,拉入一群看倌,地上的一次性台布越铺越多。参加游戏的有我、Camel、落草为寇、占山为王、Noliper、爱玲、小球、Bob、Maczhou、jessie等十余人。在地下室昏暗的环境下玩杀人有一种“人在情境中”的快感。屋外细雨霏霏、夜黑风高,地下室内杀得刀光剑影、血雨腥风。Bob是位高明的侦破者,Noliper是事后诸葛亮,Maczhou是无辜的受害者、占山为王是勤快的跟风者,我和落草为寇则是躲藏在暗处的杀人者。在我俩的通力合作下,消灭一警察,陷害一警察,杀死数位愚民。
地下室欢腾了一整夜。
凌晨两点的时候,诸人带着余兴散去了。我、落草为寇和Noliper将最后一些食物和酒消灭干净后各自钻进了帐篷。
夜又再次变得如初生婴孩一般柔软宁静。
D4 2005.10.3 雨
每次出行的最后一天,像是一个与现实接轨的临界点,我都想有意无意地跳过,或者让它永远迎候在前,不曾来临。
睁开眼睛的时候,又是大伙儿已经在整包的时候。Camel给扎营的地方留了影,我们地下室的一伙就匆匆离开。
车轮滚动的刹那,空气中有些细碎的离愁别绪开始弥漫开来。这只是一段旅途,来告别吧,和那座没有登顶的山,和那些可爱的人。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会遇上很多人,每个人只陪你走一段路,之后迅速分开,然后出现第二个,继续陪你下一段。交集过后,各归各位。倘若是之后在城市中再次邂逅,也许感觉已不似从前。我明白,我们可能会有一致的远方,但不会有共同的终点。所以,不必奢求。
camel突然问我:为何昨天会头也没回地决定继续上山?我答不上来,也许是想成为不一样的人——我希望变成的那种人吧。我明白“适时放弃”的道理,也明白她说的“天不时地不利”的特殊状况,但我想做的仅仅是征服我自己,征服自己脾性中的那些弱点和那些沉闷着不愿启齿的懦弱。所以,请原谅我的倔强。虽然,最后还是没登顶成功,但是,也没有遗憾。因为,山,它永远在那里,我们依旧可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站在山巅高呼,将瑰丽的景致尽收眼底。
下午三时许抵沪,徐家汇人头攒动。我依旧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一时难以适应。那一座座山、一条条溪是每个人心中的“潮音海滩”,也是通往理想彼岸的一根根绳索。但我们,终须回来。
“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当《旅途》的音乐再次响起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开始逐渐淡定,并在这被霓虹灯压缩过的稀薄空气中,开始为下一次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逃离做着准备。
2005年10月6日 PM15:05 完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8 0:05:4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