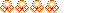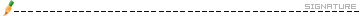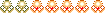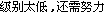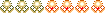文字版本
当我重新回归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心中涌起莫名的怆然,仿佛这里才是异乡,我正在与我该有的生活状态背道而驰。似乎兔子原本该是吃肉的,吃回它的青菜萝卜才是它的悲哀。就连下了飞机跑出调度车的间隙,身上粘着的暑气都让我浑身不舒服。在拥挤的夹杂着香水味、汗液味与狐臭味的车厢里,我不由开始嘀咕:上海果然比北京热多了。仿佛我只是个初来乍到异乡客。或许,明天的我就会背上公文包,蹬上细袢儿凉鞋,洒上试用装DIOR香水衣冠楚楚地坐在我俗气的办公室里。也许这样才是生活。但请允许我今天再做一天的愤怒青年,暂且抛开那些黏腻的吴侬软语,对日渐腐烂掉的生活比出我的中指。
我想,在北京安然度过的五天是让人难忘的,像一个孩子一整个愉悦的暑假一般让人回味。重新背上书包的那一刻,这个孩子会比较怀念假期一些,还是会更加憧憬新学期一些,谁也说不准……
出发的那天的航班延误是导致停留北京那几天日夜颠倒的*。我睡意阑珊地坐在几乎躁狂的候机大厅里,几乎所有九至十点档的班机由于上海下午的一场雨全体延误。飞去海口的乘客与机场工作人员正唇*舌剑地争吵,个个都是严肃的表情,只有撒在地上的十几份盒饭在咧着嘴大笑。
我的大脑告诉我,这个时刻我不该继续醒着,要醒,至少该在梦中醒着。憋了很久,起身走进厕所的那一刻,广播里开始唤人登机,我欢欣鼓舞。
飞机出上海的那一刻,地面上的灯光就像说好了一般全体消失了,好象是被人猛得拉去了开关。我转过头去对SUN说:飞机起飞的感觉就像是锦江乐园里的云霄飞车上升时的预示。我在想,我们将飞去哪里呢?是北京还是天堂?
飞机抵达首都国际机场的时刻已经是北京时间一点整,我摞了摞额前的乱发,背起我30公升的旅行背包跟着人群走出蜿蜒的通道。感觉很奇怪,我那连洗手液、感冒药、护创膏等杂物都统统塞进去的背包,居然像个初生的娇弱婴孩一般静静地趴在我的肩头,轻柔的,飘忽的,一点儿也不沉。
搭上机场巴士,中途倒出租到了学府园,北京凌晨的马路很静,几乎能够听到浮尘微粒在空气中上升的声音,以至于我像一个被母亲的双臂环绕着的充满安全感的幼儿一般,可以沉沉地在任何交通工具上睡着,安逸的。即使有人推醒我,我都满足地不抱任何怨意。
老哥和爽来接我们。爽瘦了很多,出落得更加标致。老哥形容我最多的词就是“小样儿”。知了叫得很欢腾。舒畅宾馆居然有愚蠢的“会客时间”的规定。爽他们只在房间里逗留了半小时就被服务台的电话催走了。躺下的时候是四点,这个时候,我在上海的爷爷奶奶已经醒了。
昼伏夜出的北京夏天开始了,我似乎陷入了比大学时候更甚的混乱状态,在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睡下,下午烈日当空的时候醒来。一切如此的自然,我又重新变成了夜的孩子,在午夜与凌晨时分,我的灵魂为自己唱响最动人的圣歌,美得让人落泪,血液的奔突汩汩有声,似乎要将体表的皮肤都掀翻。北京夜里的知了有最清冽的嗓子,你一定不知道。
先是SUN准备在时隔一年之后会会他的同窗们,事实上这是我们首都之行的主要目的,可惜很多人都不相信。很久没有喝酒的我又再次捧起了酒杯。几杯下肚之后,脸上的几抹红晕继而转向绯红,这几乎是我每次喝酒必有的过程,我又一次狠狠地怀念起Frank来。在他去爱尔兰之前,我们这拨人在每个夏天势必拼死海喝一通,在灌下十几二十杯红酒之后,一伙人还手拉着手,在马路上走成一字型,奔赴溜冰场,老远就能看到一群醉醺醺的小屁孩儿瞪着猩红的双眼东倒西歪得在大街上左冲右突。场面十分壮观。
SUN的号召力着实了得,大凡叫上的人都悉数赶到,觥筹交错好不热闹,仿佛分别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对爽说,我们同在一个城市的室友们都未必能召唤得起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事情在忙,曾经的同僚们现在都在自己之外的空间里好好地生活,彼此的联系似乎都成了一种打扰。
我的NIKON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没电得太不是时候。这时,我总算明白:要将记忆定格在脑海里,原来是出于情非得以的自我安慰。
北方鑫柜的一夜欢歌,可乐、爆米花、摇滚老大连续三遍的《热情的沙漠》、老哥浑厚的好嗓音是这个喧闹夜晚平和温暖的插曲。
凌晨五点,走出鑫柜大门,清冷的风拂过每个人明朗的发际线。我像个练舞的孩子,想系紧鞋带,在这没有方向的风中开始跳舞……
天亮说晚安。
北京的的士载着每一个孩子奔赴他来时的地方。打表的时候,一盏盏尾灯也同时熄灭了……
我开始对这个城市衍生出丰富的情感,典型性路盲症的我开始对一些地方出奇的熟络,似乎我的大脑里注定留出很多空白的地儿让它们挨个儿填上,例如积水潭,例如德胜门,例如鼓楼,例如联想桥,例如新街口,例如二里庄……无论是在婆娑的树影还是烈日的炽烤下,我都穿着我的花裙子以一种安然的心态和膜拜的姿态走过一条条大街小巷……
这一趟,我终于在北京遇到了沉淀和米米。在上海的两次碰头似乎都让我习惯了同一种的见面模式,而这一次以客人的身份出现似乎更让我贴近骨子里的自己。
一些孩子都迅速地长大了。
后海的华普超市后门,当沉淀扯着嗓子大喊一声“女人”的时候,我循着熟悉的声音一眼望去,还真辨认不出人群当中哪个才是她了。当我追问着北京当地还有哪些6TO京城派典型人物的时候,她想了想,告诉我:真的不多了,都走了。眼睛里似乎有一点点斗转星移的悲怆,又似乎有一些阔别已久的感慨,也或者什么都不是。
当初的大部分元老现在都已经不太写字了,青春期的躁动和那些可以任意把玩的忧伤已经不容分说地湮灭在现实的废墟及生计的需求中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诉说的能力。人总是要长大的,剩下的人将是孤独的。又有谁甘愿孤独?当初的冲动和“为赋新辞强说愁”都已被羞赧地小心掩藏起来,而如今厉害百倍千倍的艰辛与痛苦则被*得如同河面冰层下的潜流,暗自奔突,湍急却发不出声音。我们用隐忍作为成长的代价,还乐呵呵地庆幸它并不昂贵。
沉淀打趣地说我太小资了,我辩解说:其实我的骨子里是愤青。她乐了,说我这样的年纪,再愤怒的话,就太幼稚了。想起某某说过:青春期过后,更多的人不是死于死亡,而是死于麻木。
我们挑了一个据说特漂亮的驻唱歌手是沉淀的熟人的酒吧坐下,最终发现大抵美女的歌唱技艺都不如她的外表。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开始慷慨激昂接近豪迈地大谈从前,沉淀说到“那些都是当年呼风唤雨的人物啊”的时候,我重复了一遍,然后谁都忍不住笑了,特猛烈。然后又开始说到霍艳、塞宁、郭敬明等一斑孩子,感慨时光如梭。
后海的夜就如同一段微颤的华彩,华丽而凛冽,又如同一个充满橙色气体的玻璃球,暧昧而美好。操着各种口音招揽客人的酒吧服务员向我吐着我爱听的字儿:美女免单,里面请。就差上前拉我的胳膊。五光十色的招牌像一张张风格迥异的脸,火树银花的灯火不眠不休,预告着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派对,是一场海纳百川的盛宴。
我在什刹海的此端和彼端之间忘情地迷失或寻找。
这个夏天的什刹海完全不像那年冬天我看到的样子。沉淀和刘恒说着一模一样的话:三里屯的那些酒吧大多都搬过来了,只是这里比三里屯更干净,也更安静。落雨说得一点也没错:后海是个特文艺的地儿。
这个夜晚,我感觉到,我熠熠闪光的草率青春还在那里。
离开后海的时候,我的脑里再次想起汪峰的《晚安,北京》。
晚安,北京。
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图片版本
StyleA...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机票上赫然印着。看着便很欢腾。
从上海出发的时候。看到机场的显示牌上这个城市的北纬的东经。
我想着:我要在地图上平移多少?
德胜门。将军出征得胜归来必到的地方。
老哥怕晒。带着我们在楼后留影。我将这蓝得透水的天看得更清楚。
我也要做一回将军。
后海某酒吧。绣花桌布和喜力。
我爱上了这酒。爱上它翠绿的身段。
SUN、咩咩和刘恒。
我说刘恒有点像摄影小青年小陆。
夏天的北京像个梦境。
但只有会做梦的人,才更懂得真实。.
.
.
StyleB...你会在这样的灯光下邀我跳舞么?
新街口上的宠物店。卖的是各类龙猫和仓鼠。这是传说中的龙猫。体形很大。嘿嘿。
老哥总说我爱把镜头对准在他们看来不值得一拍的东西。
长安街上某大院门前的花正绚烂地开放。
想摘一朵插在发际,被及时制止。
菖莆河公园里的红鲤鱼。
凶悍的管理员禁止我近距离拍摄,他该不会认为我的相机对鱼儿有辐射?!
夏天夏天,借我一张明媚的脸。
我更愿意相信刚毅矫健的卫士也在等待着伊人的回归。
也许是看厌了单纯的英雄主义。
当我按下快门的刹那,SUN用伞挡住了华表。它似乎就这样休憩了。
静谧中,我心如止水。
o.v.e.r>>>[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5 11:57:34编辑过]